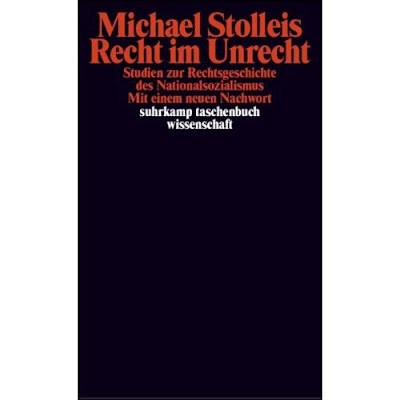
針對Maunz事件,Michael Stolleis在1993年4月,曾於期刊「批判司法」(Kritische Justiz)上寫了篇簡短評論,該文原名「Theodor Maunz-一個國家法學者的一生」,之後被收錄在Stolleis於1994年出版的「不法中的法 - 納粹法制史研究」。對這個讓許多人難堪的「醜聞」,Stolleis以公法學思想史研究者的身分,提出了他自己的觀察。
※ Michael Stolleis其人
1974年至2006年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曾任浦朗克歐洲法制史研究所所長,為當代德國法學界治公法史之大家,其代表作「公法史」(1988初版)幾可列入該國法史學經典之林,Stolleis氏並曾以此作,於1991年獲頒向有德國諾貝爾獎別名之萊布尼茲獎
I.
Theodor Maunz(1901-1993)現在終究成為德國國家法學不能不面對的道德困境。那些一部分埋藏在未詳加檢視的過去、一部分被認為已經獲得補救並且看起來得到寛恕的事物,現在又再次以令人難堪的方式重現。
「Maunz事件」本來看起來已經結案。對於這位在1993年9月10日過世、備受愛戴的沉默老者,相關的訃聞都已寫就,當中並無任何讓人驚異之事。大體上來說,觀諸Peter Lerche在1988年C.H.Beck出版社出版的祝壽論文集「一個法律人的肖像」中所作的頌詞,即可知其大概。在這篇頌詞中,Lerche用一種極富技巧性的委婉表達方式,將Maunz這三十年來已為眾人所知的納粹過往輕輕帶過。這麼做當然不漂亮,也說明Lerche並未坦率地撰寫這篇頌詞。不過,無論如何,Maunz當時仍然在世,而且這本來也不是什麼學術作品,只是為「祝壽論文集」所寫的短文罷了。
確實,有著納粹過往的教授並不算鳳毛麟角,這當中沒有人像Maunz一樣因為文化部長的身份而受創如此嚴重。關於他的一切早在1964年就已為人所知,爾後又逐漸為人所淡忘。對於那些當時尚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世代而言,由Gerhard Haney、Konrad Redeker、Hildegard Hamm-Brücher等人所誘發的「Maunz事件」,跟Obländer事件、 Globke事件、Pölnitz事件、奧許維茲審判、艾奇曼審判一樣,都屬於戰後世代的自我發現,也因此成為世代衝突的「佐證」。由這些事件和審判所滋養的,對於官方說法和掩飾的不信任,促成了1968年學運的暴發。
Maunz可說是天生拿來作例證用的:他那部四平八穩的、當然也稍欠啟發性的教科書「德國國家法」,如同福斯金龜車一樣,彷彿聯邦共和國的堅實典範-當然,也像金龜車一樣,其根源可追溯至第三帝國。「Maunz-Dürig基本法註釋書」幾乎可說是新國家的憲政神諭。「教皇Maunz」是慕尼黑大學的一個建制,享有所有公法學的光芒。如Peter Lerche所言,他是「無人可比的教導者,溫和的檢驗者,有著過度的寬容」。良善、誠摯、非凡的勤奮和自我紀律、寛容、貼近現實、不具任何學術偏見,這些優點他通通都有,沒有任何熟識他的人會否認這一點。「到目前為止,其他人所給予Maunz的禮敬,還遠遠比不上Maunz給自己的禮敬」(Lerche 語)。
保持一點距離來看,這樣的確信或許是說得通的,但從學術思想史上來看,在以Maunz為名的數百部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一部是建立在獨立思想上的。我們必須坦白承認,Maunz那些針對現行法而完成的著作,幾乎沒有一部是有原創性的,相反地,只能視為溫和的、避免衝突之通說見解的體現。對於這點,法蘭克福匯報是用一種很微妙的方式指出的:「這些著作的特出處在於一種專注重點、強調實證的簡約性」。我們至少可以注意到,批改學生作業時所表現的「無比寬容」,有拉高上課人數的正面效應。不過,先放下這些疑慮不談,有一件事到不久前為止是沒有爭議的:Maunz固然有著不容否認的納粹過往,但是透過他與民主政體的積極合作,以及無私編訂適於聯邦共和國應用的國家法和行政法,這段往事一直被認為是已經被克服的。我們或許真的可以用一種崇高的聲音說:「他的名字算是德國國家法學中最重要的一個」(法蘭克福匯報)、「我們不可能讚頌今日的公法學,而不同時讚頌Maunz」(Lerche)。
當然,有一些頗具代表性的謎團並沒有得到解答。早在1934年就有評論家注意到,Maunz巧妙地轉變他在1933年還跟Carl Schmidt截然兩立的觀點,以一種極為懊悔的姿態投入Carl Schmidt式的秩序思惟。1932年Maunz還在強烈主張法與政治的分離,而且反對「透過既有權利保障的分解造成個人法律地位的減損」,而今身為大學助教的Maunz正在等待晉升為教授職,並且開始強調法的政治本質,以及領袖意志的絕對性。彷彿為了證明個人對黨路線的絕對忠誠,Maunz在1936 年-儘管其學生Hans Nawiasky早在1933年前就因為猶太人血緣而成為反猶仇恨宣傳的最重要對象-以演說者的身分出席「法學中的猶太種族」研討會,並且在會中闡述「猶太裔行政法學者對於自由法治國教條的危險傾向」。1937年,他終於獲得弗萊堡大學的教授任命。出生於Dachau而且有著行政實務經驗的Maunz很清楚,當他在講堂內以「合法律性」的概念代換「合法性」時,當他宣稱「主觀公權利的終結」,當他將蓋世太保的拘捕措施界定為不受法院審查的高權行為,這些論點實際上意謂著什麼。就在同一時期,他沒有切斷與教會的聯絡,而且在一遠離弗萊堡公眾的黑森林小鎮參與禮拜天彌撒,這看起來算是一種有遠見的自保策略。因為在納粹體制敗亡後,Maunz馬上就可以跳到基社聯盟黨的陣營,作為專業鑑定人為「西南邦」奮戰,參與基本法的諮詢工作,撰述「德國國家法」,最後在 1952年被任命為慕尼黑大學教授。這時候的Maunz一開始只是基社聯盟黨的「陽春黨員」,過不久就被任命為巴伐利亞邦文化部長。Maunz就是如此這般的,重新回到他一開始的出發點,亦即議會民主和法治國體制。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