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胖普常說我記性好,可以記得很多零星瑣碎的事情。要我自己來解釋的話,這種能力(?)可能得力於從小對歷史讀物的偏好,所以對於某些重大事件的枝微細節記得特別清楚。當然,事件重大與否完全取決於我個人的主觀,因此有可能是四年前粗心大意養死一隻幼喵的慘痛經歷,也有可能是跟個人史完全無關,但學校教科書一定會寫的事件,比方說蔣經國之死就是。小蔣之死對我來說就好像奇士勞斯基原色三部曲一樣,是由好幾個不同顏色串起來的場景。
四姨丈淺藍色日產青鳥的行李箱:家父家母本身是公教人員,日常的親朋往來圈也都那麼理所當然地以公教人員為主,從商的四阿姨和四姨丈可說是少數的例外。他們的特殊性不但表現在職業上,也表現在政治立場上,從八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到現在執政已近八年的DPP,他們始終投以支持。如果要作政治定性的話,四阿姨一家無疑地屬於那種被自主公民和親綠學者們照三餐鄙夷辱罵的所謂深綠基本教義派。他們當年的政治行動仍為我所記憶的,就是義務發送每期出刊必被警總查扣的黨外雜誌,四姨丈那輛裕隆製淺藍色日產青鳥的行李箱也就常常散置著不同期次的黨外雜誌。小蔣死前不久家母在台北的親屬們一起吃了次飯,因為人多我必須坐到四姨丈的車上,下車時驚鴻一撇瞄到行李箱中的某本黨外雜誌,封面圖片是坐著輪椅的偉大蔣總統,題字大約是「蔣經國大限將至」之類的。對當年一個初受黨國教育未久的小學生來講,此等圖文帶來的衝擊直逼後來讀國中時看到平生第一本色情雜誌的程度。長大以後才知道,原來那是小蔣死前前一年年底抱病出席國民大會的照片,會中DPP的國代在御前放肆地舉起了布條嗆聲,因糖尿病失明的年邁獨裁者雖然未能在第一時間了解騷動的來由,但在隨從轉述下仍大感不悅。郝市長的爸爸後來在自己公開出版的日記中,還把這場風波歸結為小蔣稍後驟死的直接原因。
旭光牌日光燈豔白色光芒照耀下的老家客廳和餐廳:家父一直有個不知從何而來的理論,認為多管日光燈的強光既省電又能照顧小孩子的視力,所以家裡每一個居住空間的正上方都懸掛著旭光牌日光燈,以及日光燈帶來的白豔豔光芒。小蔣死的那天官方當然沒有在第一時間公布,甚至到了每天七點整固定播報半小時的三台晚間新聞也沒有揭露,一直到了八點連續劇播了大概半小時的時候才以新聞快報的方式告知臣民們今上大行的訊息。那齣連續劇名曰「還君明珠」,講的大概是劉松仁和蘇明明所飾演男女主角多年苦戀的故事,可說是典型用來賺人熱淚的大時代小兒女愛情肥皂劇。新聞快報插入的時點我還記的很清楚,在佛寺中修行的劉松仁因為某事而決定斷髮出家,到寺中探視的蘇明明聞訊後大驚,手中拿著的一袋水果隨手鬆落,一顆顆蘋果就這樣沿著寺中的階梯滾滾而下,就在這讓所有觀眾內心為之糾結的一瞬間,宣告小蔣過世和李登輝依憲法繼任種花民國總統的快報就這麼不識時務地插了進來。我會記的這麼清楚,可能跟我那晚違反家母嚴命不作功課偷看電視以致於腎上腺素大量分泌有關。以後回頭想想,如此這般的場景其實還挺逗趣的:二十吋電視機,楊佩佩製作的愛情肥皀劇,獨裁者的死訊,全神貫注在電視螢幕上的中年婦人,掩蔽在客廳一角偷看的小鬼以及閃耀著整間客廳的白光。關於旭光牌日光燈的故事沒有這樣就完,小蔣死後幾天,同樣在白光照耀下的餐桌上,家父家母交換著我長大以後才能解讀其政治涵義的對話,像是:「這次好奇怪,沒有像上次那樣天地出現異象」、「李登輝沒有喝過海水,那些外省人甘會服他?」。
昏黃色路燈下的仁愛路行道樹:小蔣死後如同老蔣一般,舉國臣民皆得到恩准「瞻仰遺容」,只不過老蔣遺體是放在國父紀念館,小蔣是放在大直忠烈祠。家父家母作為黨國體制的螺絲釘當然不會置身其外,在前往大直行經仁愛路復興南路口時,在家父的裕隆製速利一點二車上,我從收音機整天播放的公式哀悼節目中聽到了那段純然發之於至誠的男人哭聲。那是時任台北市長又或者是內政部長的許水德哭聲,許水德極為哀戚地陳述了已故偉大蔣總統的偉業及其施與人民的豐厚恩澤,親耳聽到的人絕對會相信這不是一種政治作戲,許水德多年以後在沒有實質政治利害關係下又哭了一次可以說是最好的證明。我會記得這件事大概跟傳統漢文化極力否定男人有哭的權利有關,家父家母從小即大力教誨男人有淚不輕彈的道理,所以許水德在這種公開場合啼哭極為深刻地在我的童年記憶裡留下了一筆。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許水德哭的那一刻是在美麗的福華飯店前,在昏黃色路燈伴隨的仁愛路行道樹下。
灰白色的基隆河高堤和深藍色的學生服:那時候到大直瞻仰遺容的人可能跟現在到台北101前過跨年的人一樣多,所以排隊是必然的,我們全家早早就下車加入了人群。人群在夜色下沿著明水路旁的基隆河高堤迎著寒風緩緩前進,我還記得,排在我們前面的是兩個穿著綉有「麗山」字樣深藍色學生服的中學女生,她們一路上沒有一刻停止竊竊私語,但對一個隨著時間過去越發不耐的小學生來講卻理所當然地成為好奇目光(?)的投射對象。後來才知道,麗山原來是內湖地區的一所私立中學。好不容易拖著打結的雙腿進了忠烈祠後,身為臣民者當然還是不夠格近距離親炙馬甜甜口中那位開明專制關心民生的所謂親民獨裁者,我們隔著巨大中庭遠距離望著另一側那具經過專家精心調製過的軀體,其週圍密佈著黃澄澄的菊花,還來不及看清楚,後面的人群很快地就把我們推出了中庭外,整個瞻仰遺容的致敬行動也就這麼令人沮喪地畫上了休止符。這麼多年以後,當聽到別人談起當年蔣幫國民黨營造兩蔣個人崇拜的荒謬可笑時,拜這段不甚愉快經歷之故,通常我心頭第一個浮起的不是什麼精緻的堂皇論述,反而是:當年那二位漂亮的麗山姐姐,今日又在何處呢(羞)?
Thursday, November 29, 2007
Wednesday, November 21, 2007
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三):歐洲的黑暗之心
這篇評論原先刊載於今年9月17日的南德時報,題名為「歐洲的黑暗之心」,評論者是柏林政治與學術基金會(SWP)的工作人員Oliver Geden,他的專著「右翼民粹主義的言說策略」最近才剛出版。與納粹德國有關的議題是德國公共領域中絕對必須萬分謹慎處理的東西,稍有不慎者即有滅頂之虞,除此之外,德國人對於週邊國家的極右翼浪潮向來亦萬分關注,Geden的這篇短文可算是這種應對態度的具體展現之一。
德國人固然對跟極右翼有關的事物極其敏感,但其週邊國家似乎並不儘然如此,極右翼政黨往往可以堂而皇之的在言論市場上爭取選票。說到底也許這才是民主國家應當盡量其開放意識形態光譜的常態,德國反而是種例外。原因當然是可想而見的,這是德國從二戰結束時起就必須擔負起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的原罪,不過這也正是我長久以來的疑惑。說到這種將種族主義的世界觀付諸實現而釀致的罪行,德國為首謀固然亳無爭議,但週邊國家恐怕也很難雙手一攤說與我全然無關吧!集中營的看守者多半是波羅地海三小國的招募人員,波蘭人曾參與鎮壓猶太人發起的華沙抗暴,寫作安妮日記的安妮很有可能是藏匿處附近的荷蘭居民告密才會在戰爭行將結束時被捕,維琪法國、義大利和匈牙利配合德國老大哥的要求輸運境內的猶太人到集中營,奧地利作為第三帝國的一份子親身參與種族戰爭,瑞士負責擔任德國掠奪財物的經理人,梵諦岡握有實證亦不願號召天主教徒挺身反抗Holocaust,身為戰爭對手的英國即便明知其事,亦出於某種不明原因而未動用空權轟平東歐的滅絕營。用刑法學的術語來講,這些國家不是共同正犯、幫助犯,就是不作為犯,而如果他們因此必須或多或少共同承擔種族滅絕的罪責,那又如何能夠同時若無其事的聲言:作為民主國家必須對所有光譜上可能的政治意識形態保持寬容,即便這樣的意識形態有可能是種族主義取向的?
Das dunkle Herz Europas
Oliver Geden
這張海報彷彿出於孩童之手,但卻足以攻佔全世界新聞的頭條。三隻可愛的小綿羊,穩穩地站在瑞士的土地上,把第四隻羊、一隻黑色的羊踢出國界。擁有27%得票率,不僅是瑞士聯邦最大黨、還是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最成功代言人的瑞士人民黨(SVP)想要「帶來安全」。聯邦司法部長Christoph Blocher主導的瑞士人民黨要透過公民投票創制法案:犯罪的外國人必須強制被驅逐出境,未成年外國犯罪者的父母也必須接受相同的處分。
Zürcher Flügel對抗菁英(註)
瑞士將在10月21日選出新的聯邦國會。對右翼民粹主義者來說,勝選的利基正是在於赤裸裸的露骨主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該黨的選戰主軸現在在國外引發了什麼樣的反應。聯合國人權專員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要求撤下這一個競選廣告。英國報紙將瑞士人民黨的提案稱之為「納粹手法」,並將瑞士更名為「歐洲的黑暗之心」。不過,如果就這樣認為瑞士人民黨會因為國際的批判聲浪而有所退縮,就未免太過天真了。相反地,該黨更加強調「反對外國干涉」並且宣稱,此一選戰主軸將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更加頻繁地使用。
如此這段的爭議在這二十年來,始終屬於西歐各國選戰中反覆上演的戲碼。只要在右翼民粹主義能夠有所作為的國家,國際的指責聲浪就要一直持續到投票日為止。在Jörg
Haider帶領的奧地利自由黨(FPÖ)與他黨短暫聯合執政終而失去選民歡心前,該黨一直獲得外界最多的關注。如果我們好好比較奧地利自由黨與瑞士人民黨的選戰訴求,則下述問題就顯得無可迴避了:為什麼這種阿爾卑斯右翼民粹主義的瑞士變種未能在德國獲得同等的注意?
瑞士人民黨跟奧地利自由黨一樣,並非全新的民粹主義產物。該黨始建於1971年,其前身更早在1930年即進入政府參與國政。不過直到Christoph Blocher主導黨務,該黨始由農民政黨轉型為保守民族主義對抗「政治菁英」的中心。從Blocher所屬的Zürcher Flügel支配黨的路線時起,該黨即獲得顯著的成長。從1999年起瑞士人民黨一直就是最受選民偏愛的政黨。該黨已經超過十年之久以不同形式主打同一的選戰重點:藐視外國人和政治庇護申請者、指控過高的稅收、誓死捍衛瑞士的獨立。
歡迎憤怒
瑞士人民黨想要更嚴格的入籍規定、政治庇護法和外國人法,支持廢止反種族主義法,要求禁建清真寺,動員對抗「社會寄生蟲」和「假殘障者」,也熱烈地與所謂的「社會建構」戰鬥。對該黨來講,加入歐盟意味著瑞士的滅國,他們懷疑躲在國際法背後的都是想要奴役瑞士聯邦的「外國法官」。瑞士人民黨持續地在政治上有所展獲,與其說是其三大政治綱領具備民粹性,不如說是作為其所有政治文宣基礎的民粹語言:「貪腐的菁英們」要對一切的弊端負責,對抗自己的人民正是他們的陰謀;政治菁英們聚斂無數,為外國的利益服務,偏袒社會中的少數;惟有人民黨站在人民的這一邊,護持「極大多數人」的利益。藉由一連串的衝撞禁忌和人身攻擊,瑞士人民黨成功地利用其他政黨與其劃清界限的大動作。當對於該黨的批判越強,極端化的效果也就越高,我群的認同也就越穩定。
作為執政黨,瑞士人民黨亦無須偏離其一貫的方針。在一個僅立基於鬆散約定而非正式聯合執政協約的政府中-與也曾經極端無比的Haider奧地利自由黨不同-該黨不會因為顧及其他政黨而作出痛苦的妥協。而且該黨最偏愛的戰場本來也就不是在政府或國會中,而是已經多次讓該黨得以全年處於全國關注焦點的公民投票。透過激進主張和戲劇性的圖片語言,Blocher的黨挑起人民心中的排外情緒並且再加以強化。比如說,在一次反對國會放寬入籍法兩處限制的複決案中,該黨就推出了一張以黑手和棕手伸進箱子攫取瑞士護照為主題的海報。這次複決案成功地否決了該項法律修正案民粹主義者很少外界批判提出什麼有論述性的回應,他們常把這些批判稱之為對健康人類理性的攻擊。聯邦法院曾有判決指摘該黨「與世界為敵」,人民黨在文宣裡的回應則是「人民總是對的」。
在九十年代,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與Haider的奧地利自由黨並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差異。不過他們的組織能力較好,而且不去作投機的議題設定,而是設定長期的發展策略。但為什麼在德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為什麼Haider的大膽言論常躍上德國媒體版面,而相較之下Blocher到今日都還得不到這等程度的關注?原因之一在於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國,同時其政治體系一向被認為太過複雜且缺乏動態。但原因之二則要歸究於德國對於右翼極端政黨的特殊應對態度,如果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沒有伴隨著暴力的展現,則這樣的種族主義少有得到注意。只有當反猶主義和相對化納粹過往明白顯露出來時,警鐘才會響起。Haider的奧地利自由黨都有這兩個特徵,而光是其政治理念核心「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歸屬感」對於德國人來講就已經太過足夠了。相對地,我們很難在瑞士人民黨這邊找到什麼納粹過往無害化的言論形式,該黨在1996年後對於反猶主義的論調則相當地自我節制。在1996年瑞士全國熱烈討論如何處理納粹所掠奪黃金和被迫害猶太人無主財物的議題,從人民黨的觀點來看,這檔事純然是「對瑞士的誣蔑」。
有別於瑞士和奧地利本國,瑞士人民黨和奧地利自由黨的民粹性格幾乎在德國沒有得到什麼注意。對於個別言論或文宣的道德化批判,是遠遠不能妥善應對右翼民粹主義的,例行性的國際反對聲浪只不過是直接變成右翼民粹主義拿來政治上獲利的道具。他們早早就把這些指摘納為選戰文宣的一部份。即便國際媒體把瑞士人民黨的頭人們加冕為種族主義者或新納粹同路人,他們的支持者也是絕對不會有什麼動搖的,反而還適得其反。在一個封閉性世界觀的詮釋下,這些指責聲浪只不過又是「他者」對抗「瑞士人民」大陰謀的再一次明證。
(註)
Zürcher Flügel這個辭彙超出我的語言能力之外,所以原文保留,不過猜測其用法有可能類似美國南方各州過去會稱北方人為Yankees,或者台灣中南部的居民有時會在有意跟台北市作區隔時自稱「阮下港」
延伸閱讀:
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一):(轉錄)大選逼近 白羊踢黑羊海報瑞士引發種族爭議
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二):(轉錄)瑞士大選 人民黨大勝引憂慮
德國人固然對跟極右翼有關的事物極其敏感,但其週邊國家似乎並不儘然如此,極右翼政黨往往可以堂而皇之的在言論市場上爭取選票。說到底也許這才是民主國家應當盡量其開放意識形態光譜的常態,德國反而是種例外。原因當然是可想而見的,這是德國從二戰結束時起就必須擔負起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的原罪,不過這也正是我長久以來的疑惑。說到這種將種族主義的世界觀付諸實現而釀致的罪行,德國為首謀固然亳無爭議,但週邊國家恐怕也很難雙手一攤說與我全然無關吧!集中營的看守者多半是波羅地海三小國的招募人員,波蘭人曾參與鎮壓猶太人發起的華沙抗暴,寫作安妮日記的安妮很有可能是藏匿處附近的荷蘭居民告密才會在戰爭行將結束時被捕,維琪法國、義大利和匈牙利配合德國老大哥的要求輸運境內的猶太人到集中營,奧地利作為第三帝國的一份子親身參與種族戰爭,瑞士負責擔任德國掠奪財物的經理人,梵諦岡握有實證亦不願號召天主教徒挺身反抗Holocaust,身為戰爭對手的英國即便明知其事,亦出於某種不明原因而未動用空權轟平東歐的滅絕營。用刑法學的術語來講,這些國家不是共同正犯、幫助犯,就是不作為犯,而如果他們因此必須或多或少共同承擔種族滅絕的罪責,那又如何能夠同時若無其事的聲言:作為民主國家必須對所有光譜上可能的政治意識形態保持寬容,即便這樣的意識形態有可能是種族主義取向的?
Das dunkle Herz Europas
Oliver Geden
這張海報彷彿出於孩童之手,但卻足以攻佔全世界新聞的頭條。三隻可愛的小綿羊,穩穩地站在瑞士的土地上,把第四隻羊、一隻黑色的羊踢出國界。擁有27%得票率,不僅是瑞士聯邦最大黨、還是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最成功代言人的瑞士人民黨(SVP)想要「帶來安全」。聯邦司法部長Christoph Blocher主導的瑞士人民黨要透過公民投票創制法案:犯罪的外國人必須強制被驅逐出境,未成年外國犯罪者的父母也必須接受相同的處分。
Zürcher Flügel對抗菁英(註)
瑞士將在10月21日選出新的聯邦國會。對右翼民粹主義者來說,勝選的利基正是在於赤裸裸的露骨主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該黨的選戰主軸現在在國外引發了什麼樣的反應。聯合國人權專員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要求撤下這一個競選廣告。英國報紙將瑞士人民黨的提案稱之為「納粹手法」,並將瑞士更名為「歐洲的黑暗之心」。不過,如果就這樣認為瑞士人民黨會因為國際的批判聲浪而有所退縮,就未免太過天真了。相反地,該黨更加強調「反對外國干涉」並且宣稱,此一選戰主軸將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更加頻繁地使用。
如此這段的爭議在這二十年來,始終屬於西歐各國選戰中反覆上演的戲碼。只要在右翼民粹主義能夠有所作為的國家,國際的指責聲浪就要一直持續到投票日為止。在Jörg
Haider帶領的奧地利自由黨(FPÖ)與他黨短暫聯合執政終而失去選民歡心前,該黨一直獲得外界最多的關注。如果我們好好比較奧地利自由黨與瑞士人民黨的選戰訴求,則下述問題就顯得無可迴避了:為什麼這種阿爾卑斯右翼民粹主義的瑞士變種未能在德國獲得同等的注意?
瑞士人民黨跟奧地利自由黨一樣,並非全新的民粹主義產物。該黨始建於1971年,其前身更早在1930年即進入政府參與國政。不過直到Christoph Blocher主導黨務,該黨始由農民政黨轉型為保守民族主義對抗「政治菁英」的中心。從Blocher所屬的Zürcher Flügel支配黨的路線時起,該黨即獲得顯著的成長。從1999年起瑞士人民黨一直就是最受選民偏愛的政黨。該黨已經超過十年之久以不同形式主打同一的選戰重點:藐視外國人和政治庇護申請者、指控過高的稅收、誓死捍衛瑞士的獨立。
歡迎憤怒
瑞士人民黨想要更嚴格的入籍規定、政治庇護法和外國人法,支持廢止反種族主義法,要求禁建清真寺,動員對抗「社會寄生蟲」和「假殘障者」,也熱烈地與所謂的「社會建構」戰鬥。對該黨來講,加入歐盟意味著瑞士的滅國,他們懷疑躲在國際法背後的都是想要奴役瑞士聯邦的「外國法官」。瑞士人民黨持續地在政治上有所展獲,與其說是其三大政治綱領具備民粹性,不如說是作為其所有政治文宣基礎的民粹語言:「貪腐的菁英們」要對一切的弊端負責,對抗自己的人民正是他們的陰謀;政治菁英們聚斂無數,為外國的利益服務,偏袒社會中的少數;惟有人民黨站在人民的這一邊,護持「極大多數人」的利益。藉由一連串的衝撞禁忌和人身攻擊,瑞士人民黨成功地利用其他政黨與其劃清界限的大動作。當對於該黨的批判越強,極端化的效果也就越高,我群的認同也就越穩定。
作為執政黨,瑞士人民黨亦無須偏離其一貫的方針。在一個僅立基於鬆散約定而非正式聯合執政協約的政府中-與也曾經極端無比的Haider奧地利自由黨不同-該黨不會因為顧及其他政黨而作出痛苦的妥協。而且該黨最偏愛的戰場本來也就不是在政府或國會中,而是已經多次讓該黨得以全年處於全國關注焦點的公民投票。透過激進主張和戲劇性的圖片語言,Blocher的黨挑起人民心中的排外情緒並且再加以強化。比如說,在一次反對國會放寬入籍法兩處限制的複決案中,該黨就推出了一張以黑手和棕手伸進箱子攫取瑞士護照為主題的海報。這次複決案成功地否決了該項法律修正案民粹主義者很少外界批判提出什麼有論述性的回應,他們常把這些批判稱之為對健康人類理性的攻擊。聯邦法院曾有判決指摘該黨「與世界為敵」,人民黨在文宣裡的回應則是「人民總是對的」。
在九十年代,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與Haider的奧地利自由黨並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差異。不過他們的組織能力較好,而且不去作投機的議題設定,而是設定長期的發展策略。但為什麼在德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為什麼Haider的大膽言論常躍上德國媒體版面,而相較之下Blocher到今日都還得不到這等程度的關注?原因之一在於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國,同時其政治體系一向被認為太過複雜且缺乏動態。但原因之二則要歸究於德國對於右翼極端政黨的特殊應對態度,如果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沒有伴隨著暴力的展現,則這樣的種族主義少有得到注意。只有當反猶主義和相對化納粹過往明白顯露出來時,警鐘才會響起。Haider的奧地利自由黨都有這兩個特徵,而光是其政治理念核心「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歸屬感」對於德國人來講就已經太過足夠了。相對地,我們很難在瑞士人民黨這邊找到什麼納粹過往無害化的言論形式,該黨在1996年後對於反猶主義的論調則相當地自我節制。在1996年瑞士全國熱烈討論如何處理納粹所掠奪黃金和被迫害猶太人無主財物的議題,從人民黨的觀點來看,這檔事純然是「對瑞士的誣蔑」。
有別於瑞士和奧地利本國,瑞士人民黨和奧地利自由黨的民粹性格幾乎在德國沒有得到什麼注意。對於個別言論或文宣的道德化批判,是遠遠不能妥善應對右翼民粹主義的,例行性的國際反對聲浪只不過是直接變成右翼民粹主義拿來政治上獲利的道具。他們早早就把這些指摘納為選戰文宣的一部份。即便國際媒體把瑞士人民黨的頭人們加冕為種族主義者或新納粹同路人,他們的支持者也是絕對不會有什麼動搖的,反而還適得其反。在一個封閉性世界觀的詮釋下,這些指責聲浪只不過又是「他者」對抗「瑞士人民」大陰謀的再一次明證。
(註)
Zürcher Flügel這個辭彙超出我的語言能力之外,所以原文保留,不過猜測其用法有可能類似美國南方各州過去會稱北方人為Yankees,或者台灣中南部的居民有時會在有意跟台北市作區隔時自稱「阮下港」
延伸閱讀:
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一):(轉錄)大選逼近 白羊踢黑羊海報瑞士引發種族爭議
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二):(轉錄)瑞士大選 人民黨大勝引憂慮
Tuesday, November 13, 2007
瑞士的右翼民粹主義(二):(轉錄)瑞士大選 右翼人民黨大勝引憂慮
瑞士大選 右翼人民黨大勝引憂慮
中央社記者周盈成日內瓦二十二日專電
瑞士國會大選接近完全揭曉,右翼最大黨瑞士人民黨以高於預期的幅度再度躍進,獲得大勝,偏左的社會民主黨潰敗,綠黨雖明顯成長但不足影響大勢。整體呈現向右轉,部分觀察家和媒體擔心瑞士政治體制出現危機。
主打移民與治安問題、被指控搞種族主義的瑞士人民黨,在下議院選舉中得到百分之二十九的選票,取得兩百席中的六十二席,得票率比四年前成長二點三個百分點,席次增加七席。人民黨以主張驅逐外國罪犯的「白綿羊把黑綿羊踢出瑞士」海報,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該黨以司法部長布勞赫為頭面人物,言論激烈而挑釁。它的大勝,令部分觀察家和媒體擔心瑞士的共識政治體制出現危機。瑞士聯邦最高行政機關聯邦委員會由七名部長組成,長久以來由四大黨共治。目前是人民黨、社民黨、中間偏右的激進黨各二席,同為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黨一席。一般預料人民黨會挾其國會議席數,在聯邦委員會內爭取更大的影響力,但究竟會不會影響各政黨目前的部長比例,尚難預料。國會兩院將在十二月十二日才選舉委員會成員。
第二大黨社民黨在下議院得票率百分之十九點五,較上次掉了三點八個百分點,席次少了九席,成為四十三席。激進黨得票率百分之十五點六,跌一點七個百分點,席次少五席,成為三十一席。基民黨得票率百分之十四點六,成長零點二個百分點,議席成長三席,與激進黨同席數。尚不足以進入聯邦委員會的綠黨是這次選舉的第二大贏家,得票率百分之九點六,成長二點二個百分點,不僅在下議院增加七席,成為二十席,更在日內瓦邦取得該黨有史以來第一席的聯邦上議院席位。代表各邦的上議院共有四十六席,目前選票尚未開完,且有八個邦必須舉行第二階段選舉。瑞士的國會兩院職權相等。
評論家米耶維利在「時報」上撰文表示,當前是二十年來瑞士最繁榮的時刻,人民黨主打安全議題竟能大勝,值得關注。他說,中間力量被削弱,左派潰敗,人民黨一黨獨大,改變了長久以來的均勢,恐不利和諧,很難想像以後政黨間要如何協調並重新適應新局面。他並表示,一向反歐盟的人民黨將來最大的困難,將是在如何處理與歐盟關係的議題上。
人民黨勢如破竹,連在最國際化的日內瓦邦都奪得最高票。「日內瓦論壇報」說,「連反布勞赫的最後堡壘都淪陷了」。人民黨主席毛瑞爾在昨天晚上開票局勢大好之際即放話表示,應該換掉聯邦委員會中的一些老面孔,包括兩位他黨人士及該黨內較溫和的國防部長施密德。但他的談話立刻引發包括來自黨內的反對。
中央社記者周盈成日內瓦二十二日專電
瑞士國會大選接近完全揭曉,右翼最大黨瑞士人民黨以高於預期的幅度再度躍進,獲得大勝,偏左的社會民主黨潰敗,綠黨雖明顯成長但不足影響大勢。整體呈現向右轉,部分觀察家和媒體擔心瑞士政治體制出現危機。
主打移民與治安問題、被指控搞種族主義的瑞士人民黨,在下議院選舉中得到百分之二十九的選票,取得兩百席中的六十二席,得票率比四年前成長二點三個百分點,席次增加七席。人民黨以主張驅逐外國罪犯的「白綿羊把黑綿羊踢出瑞士」海報,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該黨以司法部長布勞赫為頭面人物,言論激烈而挑釁。它的大勝,令部分觀察家和媒體擔心瑞士的共識政治體制出現危機。瑞士聯邦最高行政機關聯邦委員會由七名部長組成,長久以來由四大黨共治。目前是人民黨、社民黨、中間偏右的激進黨各二席,同為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黨一席。一般預料人民黨會挾其國會議席數,在聯邦委員會內爭取更大的影響力,但究竟會不會影響各政黨目前的部長比例,尚難預料。國會兩院將在十二月十二日才選舉委員會成員。
第二大黨社民黨在下議院得票率百分之十九點五,較上次掉了三點八個百分點,席次少了九席,成為四十三席。激進黨得票率百分之十五點六,跌一點七個百分點,席次少五席,成為三十一席。基民黨得票率百分之十四點六,成長零點二個百分點,議席成長三席,與激進黨同席數。尚不足以進入聯邦委員會的綠黨是這次選舉的第二大贏家,得票率百分之九點六,成長二點二個百分點,不僅在下議院增加七席,成為二十席,更在日內瓦邦取得該黨有史以來第一席的聯邦上議院席位。代表各邦的上議院共有四十六席,目前選票尚未開完,且有八個邦必須舉行第二階段選舉。瑞士的國會兩院職權相等。
評論家米耶維利在「時報」上撰文表示,當前是二十年來瑞士最繁榮的時刻,人民黨主打安全議題竟能大勝,值得關注。他說,中間力量被削弱,左派潰敗,人民黨一黨獨大,改變了長久以來的均勢,恐不利和諧,很難想像以後政黨間要如何協調並重新適應新局面。他並表示,一向反歐盟的人民黨將來最大的困難,將是在如何處理與歐盟關係的議題上。
人民黨勢如破竹,連在最國際化的日內瓦邦都奪得最高票。「日內瓦論壇報」說,「連反布勞赫的最後堡壘都淪陷了」。人民黨主席毛瑞爾在昨天晚上開票局勢大好之際即放話表示,應該換掉聯邦委員會中的一些老面孔,包括兩位他黨人士及該黨內較溫和的國防部長施密德。但他的談話立刻引發包括來自黨內的反對。
Tuesday, November 06, 2007
John Keeg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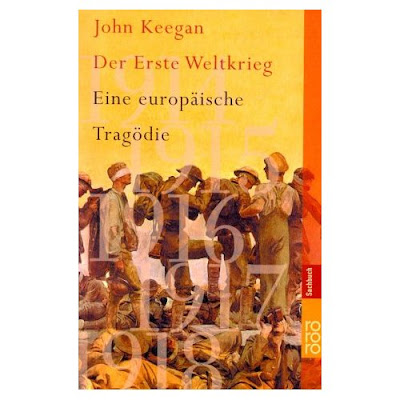
今天把John Keeg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德譯本讀完了,有些感想:
John Keegan,現年73歲的英國重量級戰史學家,歷年累積下來的相關著作,質量都堪稱驚人,對軍武迷來講(不包括我這種三腳喵),為這位老先生殺傷自己荷包的程度,套用某強者曾用過的說法,叫做「可比擬英國遠征軍1916年索穆河會戰傷亡數般的慘烈」。不過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是,Keegan著作在台灣的漢譯本並不多,我印象中就只有星光出的圖解戰史系列中介紹二戰德國武裝親衛隊那一本。這種稀少性相較於另一位英國戰史學家李德哈特就更是明顯,或許是後者有已故的鈕先鍾先生加持的關係吧。
李德哈特也曾對一次大戰作史,台灣麥田出版社大約在2000年前後出了漢譯本。另外聯經出版社在2004年為了幫自主公民們和公共知識份子們的反軍購活動造勢,也急就章地出了另外一本知名的一戰書:Barbara Tuchman的The Guns of August。這三本處理相同主題的書拿來比較,簡言之可用兩句話交代過去:戰史專業性上,李作>K作>>T作;非軍武迷讀者的可讀性上,T作=K作>>李作。李作詳細地交代了各場會戰的前後經過,K作僅述其重要梗概,比如說日德蘭海戰一事,李作以專章詳述各個時點英德兩國海軍的戰術動作,K作則僅置於海戰一章中的一節。不過這也給K作帶來了高度的可讀性,記得初讀李作時差點讀到睡著,讀K作時則有如同讀T作般的那種彷彿可以不間斷讀下去的流利感,但說到專業性和全面性,新聞記者完成的T作則又遠遠不如科班出身的K作了。所以如果就推廣一戰史這個台灣讀者相對陌生的領域來講,K作應當是三者中最為上選者,然而遺憾的是,在大師眷顧和政治考量的夾擊下,正是K作無法在台灣出版漢譯本。一個心儀已久的讀者也只有在若干年後,在國外圖書館使用另外一種語言方得一窺該書的全貌。
Subscribe to:
Posts (Atom)